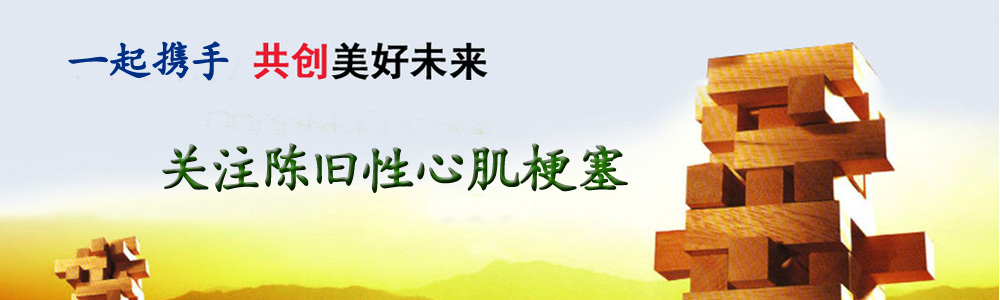毛泽东私人医生忆毛与张玉凤大吵引发心肌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我和陶桓乐正在游泳池值班,医疗组的护士余雅菊冲了进来。毛的心脏发生了大量的早跳,全身出汗,唿吸急促。开始时张玉凤不让检查,我们深恐毛是心肌梗死,坚持检查。
毛此时仍有意识,但已没有力气阻止我们进行检查。我们立刻做了体检和心电图。打电话到工字楼后,其他的医生随即赶到游泳池。心电图显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心跳不规律。经过抢救,逐渐纾解。毛的护士孟锦云和李玲诗后来告诉我们,主席和老挝总理凯山会谈完后没多久,就和张玉凤大吵了一架。
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全都赶到游泳池。他们询问完了发作的情况,当时商定,由外交部发文通知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为了使毛得以充分休息,今后不接见来华外宾。
华国锋对张玉凤说:“主席年纪大了,有重病,伺候他老人家要有耐心嘛。”张玉凤嘴里嘟嘟囔囔,很不耐烦。王洪文凑过来说:“小张,好好伺候主席,我们感谢你。”
华国锋当时决定,毛如果发生变化,立即通知他,并且提出今后毛的疾病和治疗,由华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医疗组有任何事,向这四个人报告。
晚年毛泽东被一个人气得发抖:“你骂我是狗?”
摘要:垂暮之年的毛泽东还是一个爱发脾气的老人,有一次,他跟张玉凤吵架,他对小张吼:“你给我滚!”小张也毫不示弱回应:“滚就滚,谁不让我走谁是狗!”“你骂我是狗,你……”毛泽东气得发抖,还把小张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有关工作人员。
当我捧起《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年1月第1版)这本书时,我很想弄清楚、弄明白这样两个问题:1、晚年的毛泽东是怎么样评价自己这一生的?2、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思、所想,他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论语·泰伯》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这本书里,我看到的毛泽东不是一个供在神坛里的圣人,不是一个享受着无比荣耀高高在上的国家领袖,而是一个年迈体衰、疾病缠身、行将就木的老人,他和许多老人都有共性。
晚年的毛泽东多愁善感、富有感情,例如,他在客厅里看电影《雷锋》,当画外音传来雷锋的声音:“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时,他竟然用手帕擦着眼泪。有一次,孟锦云给他读报,当她读一则新闻报道河南发生水灾时,她听到了他的抽泣声,小孟赶紧给他递消毒毛巾,毛泽东说:“没事儿,你接着读,我这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
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当他听到与自己几十年同舟共济、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得力助手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他泪如泉涌,失声痛苦“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曾对护士小李念过两句诗:“风云帐下奇儿在,古角灯前老泪多。”这两句诗正是晚年毛泽东心境的真实写照。
暮年的毛泽东依然读书成癖,他一天到晚几乎就是躺在特制带双床头的木床上看书,有时一读就是5个多小时,还一动不动地默默读着。他常读的书有《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鲁迅全集》、《考古学报》、《自然辩证法》、《笑林广记》、《容斋随笔》、《全唐诗》、《智囊》等。有一次,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一道看电影《红与黑》,观后他叫小孟去图书管理员小周那里借《红与黑》来读,并与她高谈阔论关于于连,看来,毛泽东还真喜欢“红学”,一个是中国的《红楼梦》,一个是外国的《红与黑》。
垂暮之年的毛泽东还是一个爱发脾气的老人,有一次,他跟张玉凤吵架,他对小张吼:“你给我滚!”小张也毫不示弱回应:“滚就滚,谁不让我走谁是狗!”“你骂我是狗,你……”毛泽东气得发抖,还把小张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有关工作人员,然而,他后来还是把已回家的小张给请回来,因为他晚年的生活实在离不开她。
有一次,在毛泽东的客厅里放映《宫廷秘史》,这是一部反映拿破仑生活的片子,观后工作人员议论说:“拿破仑的情人可真漂亮。”“当然啦,拿破仑的情人还能是丑八怪。”
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他们的议论说,“谁也不会喜欢丑嘛,满脸大麻子,你喜欢?”当小孟说起空军大院放一部写拿破仑妹妹的外国电影,里面有女人洗澡的镜头,每到这里,放映员就拿一张纸挡住镜头,毛泽东就议论说:“这里面有一个美学问题,看来,你们不太懂。当然,我也谈不上懂得多少。人是大自然中最完美的造化物,人体美最能从女性身上体现出来。怎么不能画,不能演呢?
晚年的毛泽东疾病缠身、心力交瘁,再加上各种事件的冲击,尤其是林彪事件的冲击,给他极大的打击,作为终身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确实感到精疲力竭、力不从心,然而,“他的心,依旧在想,依旧在思索,他的眼睛,依旧在看,依旧在环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他不甘心退出,他不愿意退去,他要竭尽全力。
也许,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以为毛泽东总是每天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着,其实,他晚年的工作就是躺在卧室的床上,穿着细布睡衣,头发不理,完全不修边幅,他用颤抖的手费劲地写字,或者干脆叫小孟代划圈。
关于看书前的那两个问题,我多少也能从书中寻找出答案。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错误,是被有巨大政治阴谋的人利用和歪曲所导致的。我们从他对江青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言过其实,说过了头嘛,不用说一句顶一万句,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也办不到呐,我说要把有的人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是撵不到,分不开嘛!”
是啊,一位风烛残年、步履蹒跚、衣食难以自理的老人,虽然,他赞成变革,赞成斗争,“人贪得无厌是不好,但人要贪得有厌,那恐怕世界也就不前进了。”,但也不会想把一场阶级革命搞成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牛鬼蛇神混杂乱成一团。
至于他对自己的评价?我们从这些话语中也可窥见端倪——“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当讲到修葺十三陵时,他说:“这些皇帝想不朽,可笑也可悲,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自己立碑,简直可恨,真正的碑应立在历史的记载上,立在人民的心中,这才叫丰碑,这才叫不朽。……”在他心里,对他自己的功与过、对与错还是交给历史,交给人民去审核。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毛泽东主席,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一代伟人,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他并敬重他。
张玉凤孟锦云为何都称毛泽东“这个人很怪”?
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与他度过最后岁月的秘书孟锦云、张玉凤回忆,在主席去世前一年,即年8月,他忽然动起看电影的兴趣,看了一出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越剧歌唱片:《云中落绣鞋》。
故事的内容大致是:一个富有员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后花园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许之为妻。有两位青年同时应召,商量好一个下井,一个用吊绳在上面照应,救出小姐后,随小姐的意愿,想嫁给谁便嫁给谁。于是一位用筐拴上绳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先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
在井外负责放筐下井的青年,在救出小姐后,为了独占小姐便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着小姐去领赏,成全了婚姻美事。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应,加上井面盖上石头,里面黑茫茫一片。青年却紧紧抓住小姐被往上拉时丢下的绣花鞋。已婚嫁的小姐一夜忽做一梦,天上飘下一只绣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丢失的一只。
梦中醒来,这位梦中的青年却出现在自己面前。结局是由父亲做主,赶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这位死里逃出的青年。至于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当然好人有好报,是神仙救他的。
毛泽东认同奸猾者
看完电影,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两位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众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孟锦云更添上几句:“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
毛泽东转头问另一位早期已在他身边伺候他的张玉凤,张说,“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吗要问这么个问题?”
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
“为什么?”众口同声地问。
毛泽东答道:“那个井下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
毛泽东的霸气
这就是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他曾写过一首《咏蛙》的诗,其中有两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17岁的毛泽东,便已显出他的霸气。
这正是毛一生主张与人斗,其乐无穷,提倡阶级斗争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思想根源。也是他在解放以后,发动一个个的政治斗争,要打倒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把与他同打江山的一些老同志清除掉。
张玉凤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就是怪,你说是黑的,他偏要说白,他总喜欢对立。”
孟锦云说,“主席的看法,老和我们不一样,这个人很怪”。
↓↓↓↓点击阅读原文快捷查看本书!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imjuc.com/xjgsys/7987.html
- 上一篇文章: 张占修急性ST段抬高性心梗补救性PCI
- 下一篇文章: 健康猝死前身体发出的信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