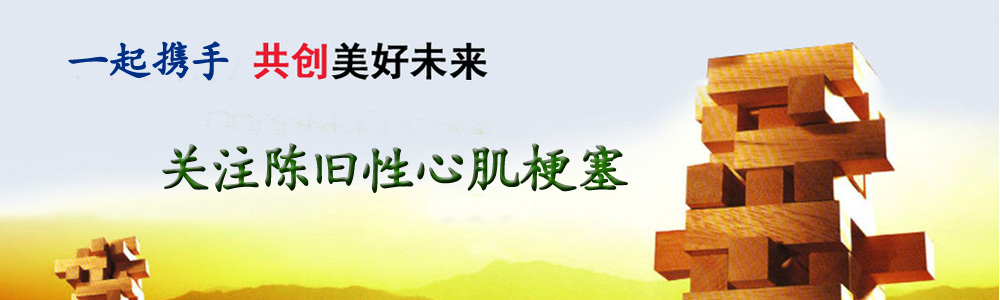急性小肠梗阻伴亚急性前壁心肌梗死患者的麻
本文原载于《中华麻醉学杂志》年第1期
一、病例介绍1.病史摘要
(1)一般情况:
患者,男性,82岁。因"腹痛6h"入院,诊断为急性小肠梗阻、肠坏死可能,拟行剖腹探查术。
(2)既往史:
冠心病史10余年,日常规则口服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及瑞舒伐他汀治疗,1月前因"四肢乏力"于外院神经内科治疗期间突发胸骨后不适症状,血清心肌肌钙蛋白T浓度(cTnT)0.59ng/L,血清肌酸磷酸激酶同工酶浓度(CK-MB)7.1ng/L,血清氨基末端利钠肽前体浓度(NT-proBNP).0pg/L,12导联心电图:窦性心律、V1-V3导联呈QS型、ST-T改变,考虑为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转入心内科监护室并予以抗血小板及抗心肌缺血治疗,未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20d后好转出院。高血压病史20余年,3级,极高危组,日常口服代文治疗,血压控制不佳;糖尿病史20余年,日常予以拜糖平及胰岛素治疗,血糖控制较差;腔隙性脑梗塞史5年余,未见神经系统后遗症;慢性肾功能不全史10余年,口服开同及呋塞米治疗。
(3)体格检查:
表情痛苦、精神萎靡。体温37.8℃,HR次/min,RR28次/min,BP64/38mmHg(1mmHg=0.kPa)。全腹膨隆,腹肌紧张,全腹弥漫性压痛、反跳痛。
(4)实验室与辅助检查:
血常规:RBC3.30×/L,Hbg/L,WBC29.40×/L,PMN百分比96.1%,Plt×/L。肝肾功能及电解质:SCrμmol/L,BUN14.6mmol/L,K+5.6mmol/L,余正常。血糖(BG):12.3mmol/L。出凝血功能:PT13.4s,INR1.12,APTT27.3s。心肌标志物:cTnT0.ng/L,NT-proBNP.0pg/L。血气分析:pH值7.24,PaOmmHg,PaCO.40mmHg,HCO3-10.80mmol/L,BE-15.10,乳酸5.5mmol/L。辅助检查:心电图:窦性心律,亚急性前间壁心肌梗死,T波改变(T波在V4、V5和V6导联倒置≤3.5mm),Ⅲ,、aVF导联Q波同导联R/4。盆腹腔CT:肝内胆管积气,腹腔内少量游离气体,肠系膜部分增厚伴渗出,局部呈旋涡状改变,部分小肠肠壁增厚伴周围积液,提示肠系膜扭转、肠壁缺血可能。
2.麻醉与手术情况
(1)麻醉前处理:
入室后面罩吸氧,行右颈内静脉及左桡动脉穿刺置管,连接Ⅱ、Ⅴ双导联心电图、SpO2及有创动脉血压监测:HR次/min,SpO%,BP64/38mmHg。血气分析:pH值7.43,PaOmmHg,PaCOmmHg,HCO3-19.90mmol/L,BE-4.4,乳酸6.4mmol/L。BG17.1mmol/L。立即启动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复苏方案,醋酸钠林格氏液扩容,静脉输注去甲肾上腺素0.05μg·kg-1·min-1及胰岛素10U/h,BP回升至/45mmHg。
(2)麻醉选择与诱导:
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充分给氧去氮后采用快速序贯诱导,依托咪酯、罗库溴铵、芬太尼、瑞芬太尼及利多卡因依次静脉注射,可视喉镜暴露声门后顺利插入7.5mm气管导管,确认导管位置后连接麻醉机行辅助通气,麻醉诱导过程患者生命体征尚平稳。
(3)麻醉维持:
以吸入麻醉为主,七氟醚维持于0.7MAC,同时按需追加阿片类药物与肌肉松弛药。使用Vegileo/FloTrac系统行CO与SVV监测,并间断进行动静脉血气分析,Hb、BG、血乳酸浓度、体温与尿量评估。继续实施EGDT复苏方案,同时辅以持续静脉输注去甲肾上腺素,使MAP65mmHg。其它治疗措施有:输注少浆血4U,维持Hb8~10g/L;胰岛素静脉持续输注,维持BG6~10mmol/L;静脉输注小剂量硝酸甘油0.05μg·kg-1·min-1;适当保温,维持体温在36~37℃。
(4)手术情况:
术中探查发现所有小肠均包裹在一囊状膜内,打开囊壁,共引流出约ml清亮液体。小肠广泛融合,末端回肠融合束带与囊壁形成纤维组织包绕卡压部分末端回肠,距离回盲部10cm小肠出现节段性坏死,累及肠段约1.6m,行小肠-小肠端端连续锁边吻合。术程约3h,术中出血约ml,尿量约ml。
3.术后管理与预后
(1)术后管理:
镇静状态下口插管转运至外科监护室(SICU),即时生命体征为:体温36.4℃,HR次/min,BP/58mmHg,SpO%。血气分析及BG:pH值7.24,PaOmmHg,PaCOmmHg,HCO3-21.40mmol/L,BE-4.6,乳酸4.6mmol/L,BG6.8mmol/L。床旁超声检查:除心尖部外其余心室节段收缩活动均正常,左室射血分数66%,下腔静脉直径1.8cm,吸气塌陷率50%。继续进行后期复苏治疗,并辅以抗感染、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
(2)预后:
术后第2天循环状态趋于稳定,拔除气管导管并恢复口服抗血小板药物;术后第5天转回普通病房;术后12d痊愈出院。
二、讨论1.术前评估
(1)评估要点:
患者因急腹症入院,病情呈进行性加重。综合现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与辅助检查提示其极有可能为绞窄性小肠梗阻并伴有脓毒性休克,具有紧急剖腹探查术的强烈指征。但患者高龄,合并多种系统性疾病,1月前突发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这些因素都使患者发生围术期主要心脏不良事件(MACE)及围术期死亡的概率大大增加。麻醉医生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临床风险因素分层并明确有无影响围术期管理的风险因素。具体到本病例,当前临床最紧迫是:①判断休克的类型:是再次心肌梗死引发的心源性休克还是肠梗阻、肠坏死所致的脓毒性休克;②制订较为合理的麻醉监测与管理方案。
(2)临床风险因素:
年,Lee等提出了Goldman心脏风险指数,使用了6个独立的风险预测因子评估围术期严重心脏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如今,众多指南均推荐使用风险预测工具来评估围术期出现MACE的风险。其中,修正心脏风险指数(RevisedCardiacRiskIndex、RCRI)因其简单易记已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风险预测工具,RCRI包含以下6个风险预测因子:①胸腔、腹腔内手术或腹股沟以上的血管手术;②缺血性心脏病;③心力衰竭;④需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⑤脑血管事件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史;⑥术前SCrμmol/L。其计算方法为:每个风险预测因子记为1分;得分0或1分提示低风险,围术期MACE发生率1%;得分≥2分提示风险增高,其发生率1%(见表1)。本例患者RCRI评分高达5分,提示该患者围术期MACE发生率11%。
(3)快速判断休克类型:
休克患者的诊治是临床医学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之一,对于可能存在多种休克病因的患者,在术前鉴别休克的类型可指导麻醉医生实施正确的围术期管理策略,改善患者预后。依据现病史、体格检查及实验室与辅助检查的综合评估方法依旧是评估休克患者的最可靠途径,但由于急诊手术缺乏或仅有极短时间行术前评估,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可能也不能立即明确休克的病因并给出最佳的初始治疗方案,因此寻找快速而有效的检查工具显得尤为必要。床旁超声可以直接"看见"患者的病理学状态或异常生理学状态,已成为评估危重症患者的新工具。对怀疑有脓毒性休克的心肌梗死患者行超声检查的目的在于:①了解心肌梗死后心脏的基本解剖结构;②了解心肌梗死后心室壁、心瓣膜的运动情况;③测量肺动脉压力与心脏射血分数;④测量下腔静脉变异率,了解血容量状况等。
2.术中管理
(1)术中监测:
对于合并有冠心病的患者,多导联心电图是监测围术期缺血的临床最简单、方便和易行的方法。联合Ⅱ导联与V3、V4或V5导联监测可提高心肌缺血事件的检出率,其中Ⅱ导联与V5导联的检出率为80%,而Ⅱ导联联合V4、V5导联的检出率更可高达96%[1]。连续有创动脉血压监测是危重病患者或高风险手术的常规监测项目,经外周动脉行连续心排量监测在使用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的情况下其准确性还有待检验。对于冠心病处于稳定状态的患者,不推荐将肺动脉导管(PAC)作为常规监测手段,PAC对心肌缺血不敏感,常规使用并无显著益处;但若患者合并有心衰、严重瓣膜疾病、混合原因的休克或其它影响血流动力学且无法纠正的潜在疾病时,仍推荐使用PAC[2]。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对心肌缺血敏感,可评估心室与瓣膜功能,在需要了解心内结构及心包与胸主动脉情况时具有优势,本例患者有亚急性心肌梗死,同时合并脓毒性休克,是术中TEE监测的绝对适应证。当然,TEE监测应由熟练掌握TEE的医生实施[3],否则必然流于形式,无法达到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的目的。
(2)麻醉诱导:
避免血流动力学剧烈波动与维持氧供需平衡是冠心病患者麻醉诱导时的首要原则,但对于同时伴有反流误吸高风险的患者,由于快速序贯诱导(RapidSequenceInduction,RSI)通常以牺牲循环为代价,因此如何使其平稳而安全地度过麻醉诱导阶段是对麻醉医师提出的挑战。对此类患者实施麻醉诱导的关键要点在于:充分的给氧去氮、合适的诱导药物及Sellick手法的使用。麻醉诱导前充分给氧去氮,可为药物起效与气管插管保留足够的时间;与瑞芬太尼相比,芬太尼与舒芬太尼虽起效稍慢,但其对血流动力学影响轻微,大剂量使用时可有效抑制气管插管引起的应激反应;依托咪酯具有良好的血流动力学特性,是合并有脓毒性休克的冠心病患者理想的诱导药物;0.9~1.2mg/kg罗库溴铵可提供与琥珀胆碱相接近的起效时间而不导致胃内压增加;Sellick手法通过压迫环状软骨挤压食管,可能有利于防止反流误吸。
(3)麻醉维持:
在确保遗忘、无意识、制动等基本麻醉要素的同时,有效抑制应激反应与维持氧供需平衡仍是冠心病患者麻醉维持阶段最重要的目标。然而截至目前,似乎并没有一种最佳心肌保护的麻醉药物或技术,多数研究显示吸入麻醉药与静脉麻醉药对预防心肌缺血和梗死发生的效果无显著性差异[4]。掌握各种麻醉药物对心脏病患者的生理与药理作用才是麻醉医师在选择药物时更为重要的依据。目前仍然推荐以大剂量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舒芬太尼)为主、辅以小剂量静脉或吸入全麻药的维持策略。
(4)硝酸甘油的使用:
硝酸甘油虽然可通过降低左室前负荷与心室腔内压力从而减少心肌氧耗,但其全身静脉扩张作用也可引起回心血量减少、血压下降、心率增快,反而不利于冠状动脉灌注。近10年来,在评价硝酸甘油对于减少非心脏手术围术期心肌缺血发生方面的研究很少,缺少有利数据支持,因此本例患者预防性静脉给予硝酸甘油毫无必要。
(5)脓毒性休克的早期治疗:
自从0年以后,Rivers等提出的EGDT策略成为严重脓毒血症与脓毒性休克患者的标准早期治疗方案。在"SurvivingSepsisCampaign"年的指南中,仍然把EGDT列为早期复苏的重要内容,具体包括在脓毒性休克诊断后应立即启动复苏治疗,并达到以下目标:①CVP8~12mmHg;②MAP65mmHg;③尿量0.5ml·kg-1·h-1;④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2)或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SvO2)分别达到70%或65%;⑤以恢复正常的血乳酸水平为早期复苏的终点。EGDT方案目标明确,记忆简单,在临床上很受麻醉医生的欢迎。随着近年来的临床实践不断增加,新的证据层出不穷。很多专家指出EGDT方案要求建立更为复杂的监测,因此治疗所需花费更多;而在早期脓毒性休克患者的治疗中,EGDT方案的疗效并不优于常规治疗方案。尽管如此,以下早期治疗的策略仍然应该遵循。①一旦脓毒性休克诊断明确,应尽早开始液体复苏。初始剂量为15~30min内输注晶体溶液20~30ml/kg,补液结束后应评估治疗效果,确定进一步的液体治疗策略;②首选的血管活性药是去甲肾上腺素。顽固性休克的患者可以持续静脉输注血管加压素0.04U/min,同时复合使用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③加强血流动力学监测。有条件应直接动脉内测压,同时监测CVP与动脉血气。对于顽固性休克患者,应尽早行心脏超声检查(TEE);④及时评估临床治疗效果。应重视基本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如意识状况、外周循环、尿量和中心静脉充盈度等;⑤以恢复正常的血乳酸水平为早期复苏治疗的终点。
(6)Hb维持目标:
心血管疾病患者对贫血的耐受性显著降低,围术期贫血将加重其氧供需失衡,导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与死亡率明显增加。以往处理高危患者或已知冠心病患者时,倾向于将其红细胞压积提高到30%,然而根据年美国血库协会颁布的最新指南[5],对于无症状的、血流动力学稳定的非冠心病患者,仅需维持Hb70g/L即可,因为宽松的输血策略并未使贫血患者从中获益更多。而对于合并有症状的,譬如胸痛、体位性低血压或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及术后患者,维持Hb≥80g/L是更好的选择。
3.术后管理
(1)管理要点:心脏病患者行非心脏手术,术后发生MACE风险最高,67%的心肌缺血事件发生于此[6]。研究显示,术后3d(24~72h)是围术期MACE的发生高峰[7],因此术后进入SICU监护是保障患者安全度过危险期的合理措施,其具体内容包括:①继续实施多导联心电图监测,提高心肌缺血事件的检出率;②测定血清cTnT水平,判断有无新发的心肌损伤;③使用床旁超声进行左室功能评估;④积极评价Hb水平,维持Hb≥80g/L,避免贫血带来的不利影响;⑤尽早恢复术前使用的口服抗栓药物。有研究指出,有效的应激管理可以降低术后高凝状态及儿茶酚胺血浆浓度,降低MACE的发生,因此制订合适的术中麻醉维持策略及术后管理方案同样重要[8]。此外,在外科出血风险减小的前提下,尽早恢复口服抗血小板药物也是冠心病患者行非心脏手术后须特别注意的问题。
本期杂志既是《中华麻醉学杂志》作为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会刊的首期,也是新一届编委会主持杂志编辑工作的第1期,其栏目内容指明了本刊今后一段时期的方向:在充实述评栏目及专家论坛栏目引导学科发展方向的同时,本刊还将着力充实病例讨论栏目的内容,更加贴近临床,面向更广大的麻醉学医务工作者。鉴于此,编委会决定委托副总编辑薛张纲教授负责病例讨论栏目的组稿、把关,进一步促进我国围术期麻醉管理的规范化建设。
参考文献(略)
(收稿日期:-01-10)
(本文编辑:彭云水)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imjuc.com/xjgsyf/9286.html
- 上一篇文章: 病例分享胡科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
- 下一篇文章: 病例分享于心亚右冠闭塞性病变的急性非